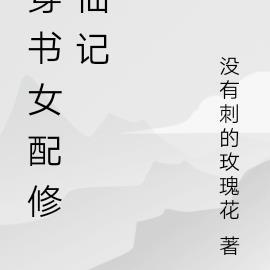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钮扣厂野餐会(第1页)
劳工节周末结束了,在河上的涡流区留下了一些杂物,有塑料杯子、空瓶子以及瘪掉的气球。时值九月,秋天开始宣布自己的来临。尽管正午的太阳还是热力不减,但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晚,而且带着迷雾;傍晚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爽,蟋蟀发出刺耳的??声。花园里长满了一簇簇的野翠菊,它们在此扎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白色的小花,还有开得较浓密的天蓝色的花,另外一些深紫色的花已经生了锈病。这要是在从前我胡乱拾掇花园的话,我早就把它们当作杂草拔掉了。如今我不再劳神去区分香花和杂草了。
现在这种天气更适合散步,外面的阳光不太刺眼。游客也渐渐稀少了,即便是那些仍在逗留的人至少也穿上了体面的衣服:不再有人穿肥短裤和紧身的马夹裙,街上也见不到晒得通红的腿了。
今天,我出发去“露营地”。我上路了,可半路上遇到了米拉开车经过。她提出要我搭她的车。说来惭愧,我当时接受了,因为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早就意识到路实在是太远了。米拉想知道我要去哪儿,以及为什么要去——她必定是继承了瑞妮那牧羊人般的本能。我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至于去的原因,我说我只是想再到那地方去看看,追忆一下过去的岁月。她说:太危险了,你永远都无法料到那些灌木丛里会爬出什么东西来。她让我保证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她,这样比较醒目。她说,她过一个小时会回来接我。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一封信——投在此地,又在彼地被取走。然而,我却是一封没有收信人姓名的信。
“露营地”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它是位于若格斯河与公路之间的一块地方——一到两英亩的面积——上面长着树木以及矮小的灌木丛,中间有一片湿地在春天会飞出许多蚊子。人们去那儿捕鹭;有时候你可以听到它们沙哑的叫声,就像是用一根木头在一只白铁罐上刮磨一般。那里,时而会有几个观察鸟类的人愁眉苦脸地到处探寻,仿佛在寻找他们失去的东西。
树荫底下,有闪着点点银光的香烟盒、被丢弃的瘪掉的避孕套,以及被雨打过的花边纸巾。狗和猫在此间立界做窝;迫不及待的恋人悄悄地钻进了树丛中,不过要比从前少多了——现在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夏天,酒鬼们睡在浓密的灌木丛下;十多岁的少年有时候会去那儿抽一些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你还可以发现一些蜡烛头、烧焦的匙子和零星的一次性注射针。这些都是我从米拉那儿听来的;她认为这种事情是很不光彩的。她知道蜡烛头和匙子是干什么用的:它们都是吸毒者的随身家当。看来,丑陋的现象到处都有。我来的地方真是个“天堂”。
一二十年以前,人们曾试图将这个地方清理干净。这里竖起了一块牌子——“帕克曼上校公园”(似乎毫无意义)——并添置了三张锈迹斑斑的野餐桌、一只塑料垃圾桶和两间活动厕所,据说是为了方便那些外地来的观光客。不过,这些人宁愿找个别的地方喝啤酒、扔垃圾,以便更清楚地观看河流的景色。结果,那块牌子被几个爱射击的小子做了练习猎枪的靶子,桌子和厕所也被省政府给搬走了——与政府的预算有关——而垃圾桶虽然经常遭到浣熊的洗劫,可还总是满满的;于是他们连垃圾桶也搬走了,现在那个地方恢复了原样。
将此地命名为“露营地”,那是因为过去这里经常举行宗教露营活动。他们在这里支起马戏团用的那种圆形大帐篷,狂热的外地牧师会赶来讲道。那时候,这块地方维护得较好,否则不知还要被践踏成什么样子呢。这里还举行小型的流动集市;商贩们设起了货摊,清理出马道,将小马和驴子用绳子拴住。一批批的游人在里面兜来兜去,最后分散在林中野餐。这是一个适合各种户外聚会的地方。
“蔡斯父子公司劳工节庆祝大会”也常在此举行。这个名称比较正式,而人们就把它叫做钮扣厂野餐会。庆祝大会总是在法定星期一劳工节前的那个星期六举行,排场很大。大会请来了仪仗乐队;自制的彩旗飘舞。还有气球放飞、旋转木马以及一些没有危险的愚蠢的比赛——套袋赛跑、匙蛋赛跑、接力赛跑(用胡萝卜充当接力棒)。“理发店”四人组的歌唱得不赖;童子军军号团会演奏一两部曲子;一拨小朋友在搭建的一个犹如拳击场的木头舞台上表演苏格兰高地舞和爱尔兰踢踏舞,舞曲的音乐是由一架手摇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另外,还有一场“最佳打扮宠物”比赛,另一场是给婴儿打扮的比赛。吃的食物有玉米棒子、土豆沙拉、热狗。“妇女援助会”出于各种帮困目的而举行自制糕饼义卖活动,有甜饼、饼干、蛋糕、果酱,还有印度酸辣酱和泡菜;每一种都贴有制作者名字的标签:“罗达什锦蜜饯”、“珀尔李子蜜饯”之类。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瞎胡闹——寻欢作乐。柜台上提供的饮料最多也只是柠檬汁,但是男人们会带来自装和瓶装威士忌。黄昏来临之时,也许会发生扭打、喊叫,喧闹的笑声穿过树林。接着,河边上有一个男人或青年被整个地扔进河里,溅起了片片水花;要么就索性将他的裤子扒掉。若格斯河的这一段水很浅,因此几乎没有人会淹死。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开始放焰火。在野餐会的鼎盛时期(至少在我印象中是“鼎盛时期”),人们还举行方形舞会,有小提琴伴奏。但是据我记得,到了一九三四年,这种过分铺张的庆祝活动就被削减了。
下午三点左右,父亲会在踢踏舞的舞台上作一次演讲。演讲总是很短,但无论是年长的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专心致志地聆听;女人们如此专注是因为她们在厂里做工,或者嫁给了厂里的工人。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就连年轻的男人也开始听演讲了;甚至身着夏装、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父亲的演讲从来不长,但你可以从他话的字里行间领会他的意思。“有理由高兴”是好事;“有根据乐观”就是坏事了。
那一年,天气又热又干,持续了太长的时间。野餐会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许多气球,也没有旋转木马了。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皱得犹如人的指关节;柠檬汁喝上去像掺了水,热狗被一抢而光。然而,蔡斯公司还没有人被解雇。生产放慢了速度,但没有解雇工人。
父亲说了四次“有根据乐观”,却没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兴”。台下,工人们的神情一片焦急。
当我和劳拉还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参加这种野餐会;现在情况却不同了,我们到场却是一种义务。我们得去亮亮相。这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母亲不管有多么不舒服,她总是每场必到。
母亲去世后,瑞妮就接管了我们。她对我们这一天的衣着打扮总是精心准备,一丝不苟。我们不能穿得太随便,因为这会显示出一种轻蔑,似乎我们对镇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讲究,因为这会给人一种摆架子的感觉。现在我们长大了,可以自己挑选衣服——我刚满十八岁,而劳拉十四岁半——不过我们已不再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了。尽管我们有了一些瑞妮所说的好行头,但过分的奢侈在我们家向来是不提倡的。不过,最近奢侈的定义变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东西。野餐会上,我们俩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过的蓝色阿尔卑斯村姑裙和白衬衫。劳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顶帽子;我自己戴的则是去年的,只是换了一条丝带而已。
劳拉似乎并不介意,而我却相反。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劳拉说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们听着父亲的演讲。(或者说我听着。劳拉是一派聆听的样子——两眼圆睁,头专注地歪向一边——但你根本无法知道她到底在听什么。)父亲以前总是能够成功地发表他的演说,不管他刚喝过什么酒;可这一次却说得结结巴巴。他将事先打好的讲稿贴近他那只好眼,然后又放远一些,目光茫然,仿佛他并未订购商品却来了一张账单。他的衣服从前都是很体面的,即便旧了也不失风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耳边的头发参差不齐,看样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满脸困扰——甚至有些凶恶,活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抢劫犯。
他演讲完毕后,人们只是完成任务似地鼓了一下掌。有些男人凑在一起,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铺在地上,坐在树底下,或者索性躺下来用手帕盖着脸,打起了瞌睡。只有男人们才这么做。女人们则保持清醒,十分注意。母亲们带着孩子们去河边,踩在小沙滩上玩水。另一边,一场尘土飞扬的篮球赛开始了;一群观众昏沉沉地在一旁观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帮她义卖糕饼。这种义卖是为了谁?我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每年都来帮忙——她正指望我这样做。我对劳拉说她也该一起来,可她假装没听到,慢慢走开了,晃动着她那下垂的帽檐。
我让她走了。我应该看住她;瑞妮从未为我操过什么心,但是她认为劳拉太轻信别人了,与陌生人太亲密了。白奴贩子总是在四处探寻,劳拉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她会上一辆陌生的汽车,开一扇不熟悉的房门,穿过一条不该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为她不分好人坏人,或者说她的判断标准与别人不一样。你无法提醒她,因为她不理解这种提醒。倒不是她无视常规,她只是把它抛在了脑后。
我老是要看住劳拉,感到烦透了,而她又不领情。我总是要对她的闪失负责,包容她的过错,这我也烦透了。我厌倦了担负责任,到此为止吧。我想去欧洲,或者去纽约,再不就去蒙特利尔——去夜总会,去社交聚会,去瑞妮的社交杂志中提到的所有那些令人兴奋的地方——但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这听起来像是终生监禁。说得坏一点,就像是一首挽歌。我被困在了提康德罗加港——一个普通钮扣的光荣城堡、一个为精打细算的购物者生产廉价长衬裤的服装城。我就呆在这个地方不动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结果我就会像“暴力小姐”那样成为一个老姑娘,招来众人的同情和取笑。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想去别的地方,然而却没有途径。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遭到白奴贩子的绑架,即使我并不相信他们。至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
第一战场分析师!
被废弃格斗机器人抚养长大的乘风,在某天接触到了传说中的机甲。乘风哦豁!第一战场指挥官!姐妹篇,行吧,听你们的用回这个中二的系列名。没什么好说的,只写校园,中篇,图个开心,看客随意...
狂神进化
一个平凡的高三学生布施瘟疫操控病毒凶虫而成长的一代传奇。...
林尘宋雪妃苏玉瑶
陪跑多年,为她打造了一切,金钱,地位万人倾慕的绝色女总裁结果功成名就的那天换来的却是无情悔婚,嫌他平凡林尘没有一丝留恋的离开,人人都当他是窝囊废殊不知旧王避退,新王低头,唯有一头潜龙,一飞冲天!!!...
当初嫌穷要退婚,现在舔我干什么
四位未婚妻嘲讽我是低配版凤凰男,退婚当天,我号令成千数万条毒蛇踏平她全族,她哭着后悔跪舔说要嫁我,晚了,你们,都得死!...
斗罗:我的武魂是十凶天角蚁
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村子,没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东青的少年,觉醒了变异武魂天角蚁,这个平静的村子,变得不在那么平静,...
风雪待归人
一场神秘的风雪后,畸变末世到来。安隅一个怕死的劣等基因贱民,因为貌似有一些神秘异能,被按头加入守序者。那是一群可怕的畸变人,慕强,残暴,好内斗。安隅初来乍到,就获得了顶级大佬秦知律的关注,守序者们为此嫉妒欲狂,排着队要弄死他。有人传言他是大佬豢养的金丝雀,传得安隅自己都信了,为了活命,每天都努力啾啾啾地撒娇。虽然这个娇撒得略显僵硬。秦知律朝他一瞥,表面驯顺。却没忍住伸手摸摸头。金丝雀首战,守序者开盘下注,押他必死。他不负众望,重度战损,可濒死之际,却丝血爆发,绝地翻盘!最高明的猎人,往往伪装成猎物存在。若唯有濒死方能觉醒,他从不介意以弱小的姿态出场。觉醒后的安隅在崩坏的世界中四处扑火,原本只想刷长官的好感,却莫名其妙地一步步成了救世神。人类基因失守,请夺回核心资源,弃城!安隅拒绝。长官的指令是拯救所有人。贫民窟大量少女失踪,幕后之人大有来头。安隅无论贵贱,一并清算。超畸体恶意篡改了一些人的时间。安隅这么喜欢时间,不如永堕循环。AI意识觉醒,大量人类被俘虏。安隅抓回服务器,重新调教。主城开始流传一本读物,守序者全体沦陷。安隅愚蠢的精神控制手段,我书名是安隅神能妄言安隅什么东西?是守序者对您的观察和总结。他们都已经加入了安隅神教。安隅谢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还有那些个本领。从头到尾,他都只为抱好长官大腿,保全小命而已。人设养狼专业户双标护崽擅长人外cosplay攻x腹黑小狼坚韧疯批在可爱和S之间灵活横跳受CP小剧场他是人间最后一隅。我会一直陪伴长官,直到我们都燃尽的那一刻。1HE成长大男主末世废土微克系2主角是神,能力对其他人降维打击但主角也有弱点,无法一直降维打击。介意慎3主角平时稳健,一失控就变S,两种状态会随着他的成长逐渐融合,并不是双重人格4两对BL副CP,一对BG暧昧,均以作话中角色碎片体现为主,正文含量轻微...